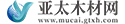刀口向内,干掉那个多嘴的人
一.
 (资料图)
(资料图)
前几天,记者李微敖举报张继科,很快就遭到了谩骂和苛责。
问句简单有力。凭什么S先生滴水不漏,景甜却大字在前?错也是张继科的,景甜犯了什么错?
甚至媒体同行都接连跳出来落井下石。千夫所指之下,仿佛最大的问题不在张继科身上,罪该万死的是李微敖。
确实,谈起「新闻伦理」,毕竟本身既无门槛,也无一定之规,以至每个人都可以多一嘴。
所谓「公共利益」的挡箭牌,真较真做起名词解释,千疮百孔只是时间问题,早晚挡不住一人一口唾沫星子。
在我看来,凭什么只藏了S先生的名头,张继科就应该化名叫做Z先生。
法律都没判的事儿,记者凭什么拿出来下定论?凭什么直接做有罪认定?难道张继科就不应该被保护吗?对张继科就公平吗?
是不是听起来还挺有道理?
风雨过去,站在雨里裸奔的,除了张继科,还剩下李微敖。
没人想过,比起保护这件事,一届白丁李微敖,连个保镖都没有,又怎么去保护自己?
二.
多嘴的媒体不止一家,这两天,三联也被架上了烧烤架。
报道聚焦天门山跳崖的四个农村青年之后,网上议论没有放过他们。
报道背后,有人看到了年轻人肉体贫困,有人看到了年轻人的精神贫困,有人看到了应该善待周边人事,有人看到了宏观大手没够到的地方。
当然,有人正提着刀找记者。
可指摘的理由我坐在电脑前都可以编出一串,譬如调查不够完整,譬如会引发模仿。
每一句指责都可以从新闻史里面找到影子,都可以振振有词,站在学界的立场上吐三联一口口水。
业内人士也开始装外宾,躺在床上开始讨论三联们为什么采访囫囵吞枣,得出的结论过于武断,似乎自己马上就要背包出发,一个月后将刊发万字长稿。
都说「说不如做」。真的,大多数时候是「做不如说」。
三.
做记者的时候,我开过一场会,台上坐着一个耀武扬威的领导,台下是一群服服帖帖的记者。
他说,为什么要报道暴力、凶杀事件?除了让人害怕,还能剩下什么?非要我每次看完你们的东西,再看三天新闻联播,才能缓过神吗?
他又说,如果一个巷子里出现了杀人案件,凶手反正都会被处理和解决,说和不说有什么区别,为什么要造成居民的恐慌?
我猛地一听,疯狂点头,觉得有理。
出了会场,回过神来,突然好奇他到底家里有没有小孩。如果有,今晚他会让小孩走那条暗巷吗?如果没有,别人家的小孩怎么办?
他本是信息的受益者。他能得到的信息,公众得不到。
四下茫然的公众看起来是安神醒脑了,是心旷神怡了,但长期来看,真的利大于弊吗?
四.
想起当年做记者的时候,每每涉及新闻伦理,总想和领导争辩。他一阵怒吼,「做就完了,回来再讨论!」
时过境迁,在媒体职业路上指引、照耀我前行的那些人,在采访路上一路前行,互援互助的那些人,如今四散零落,天涯难觅。
现在,连吼这句话的人都没了。
回过头看,满墙的锦旗屁都不是。你以为的职业准则,你以为的公共价值,你以为的道义和理想,在生活和现实的窘境里面,早就碎成了粉末。
你想帮的人在提刀找你,一起走的人在提刀找你,骑着你的人也在提刀找你。
拔剑四顾,噢,原来这就是亥下,原来四处是敌。
想想这么多年,都市报记者这个行当啊,早被逼上了天门山——山下是教你做事、做人,甚至提刀赶来互戗的同行们。
这份工作,于公于私,做到今天,不如不做。
都上天门山了,不如纵身一跃。